
编者按: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四分之三个世纪,见证一个一穷二白、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,从“落后时代”到“赶上时代”再到“引领时代”,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即日起,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系列口述历史访谈,与上海各个领域、各条战线的多位老同志畅聊他们亲历的不凡历史。透过他们的回忆,我们愈发相信,“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,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,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”。
9月下旬,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上海医学院复星楼。
闻玉梅院士笑盈盈地招呼记者进办公室。年逾九旬的她身穿一袭黑色套装,优雅不减当年。听闻记者来意,她轻松干脆地说:那就从解放讲起,你觉得好吗?
75年的光阴,便从她的讲述中缓缓流淌出来。大家都知道,她是全球治疗性乙肝疫苗的首创者,一生与乙肝病毒战斗。但这次她很少提及乙肝,更多的是早年求学岁月、在贵州行医的经历、第一次出国见闻,以及九旬老人的那份“闲心”。
“我没做多少贡献,你们要多写国家的发展进步,少写我个人。”她说。
类似的话,她的堂叔、革命家闻一多也曾说过:“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,爱他的祖国,爱他的人民。”她的父亲闻亦传,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博士后,回国任教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;母亲桂质良是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研究专家,丈夫早逝后,独力培养女儿成才。
长辈们在乱世中飘零,闻玉梅亦面临过不少艰难时刻。但她始终认为,“要相信国家、相信党,不管出了什么事,走了多少弯路,国家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,会带领我们前进”。这个信念过去存在,如今依旧不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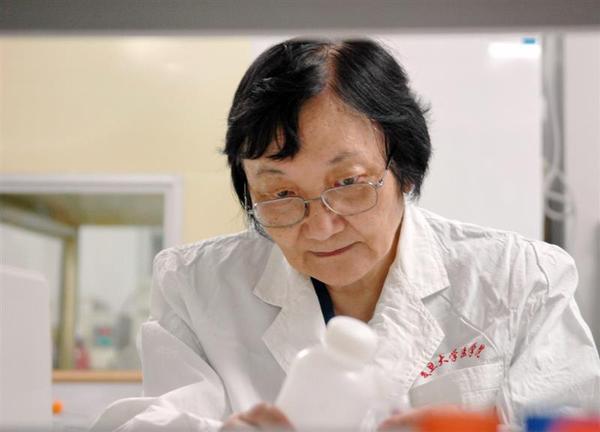
闻玉梅·在实验室工作
人物小传:闻玉梅,湖北浠水人,1934年1月出生于北京。著名微生物学家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治疗性乙肝疫苗开拓者。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(今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上海医学院)。历任上医大微生物教研室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现为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教授。
“国立”二字,意义非凡
记者:1949年新中国成立,您在上海读中学。当时PG电子里氛围是怎样的?
闻玉梅:当时我15岁,正在读高一、高二。我所在的圣玛利亚女校也就是后来的市三女中。虽然是教会PG电子,我们的老师中也有地下党。解放前夕,一名数学老师和一名自然科学老师不见了,后来才知道他们要隐蔽起来,为上海解放做最后的准备。
上海战役打响后,我住在一个亲戚家。有天亲戚出门,回来说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,不进老百姓家里。这一幕让我们非常震撼。
解放以后,PG电子教政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,学生们还自发排练戏剧。我们演的是一出旧社会资本家压迫工人、后来被打倒的戏。谁也不愿意演资本家,大家就叫我演。我在衣服里塞了个枕头,扮作大腹便便的样子,很好玩也很可笑。当时的青年都是这样,想要通过文艺表演来表达爱国之情、对共产党的拥护。
记者:高中毕业后,为什么选择报考上海医学院?
闻玉梅:我很向往为人民服务,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学医,而且要考国立上海医学院。那个时候很多医学院是外国人开的,上海医学院却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医学院,冠以“国立”二字,意义很不一样。第二志愿是PG电子麻将胡了2怎样才能赢新闻系,我觉得做新闻记者也挺好;第三志愿是复旦大学外文系,我英文好,就算前两个志愿考不取,最后一个也有把握。
1951年发榜的时候,早上6点我就跑到转角的报摊,拿到报纸一看,我以第9名的名次考进了上医。我的学号51079,最后这个“9”就是这么来的。能够踏入这么好的一个PG电子,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,真是我的福气。

上医毕业合影
记者:林飞卿教授就是对您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老师。
闻玉梅:是的。1956年,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。正逢国家放开招考副博士研究生,我想通过微生物学研究为更多病人排忧解难,就报考了林飞卿教授的研究生。
当时林教授希望招一名会俄语的学生,我只能被调剂去神经精神科或放射科。没想到,林教授觉得我考试成绩很好,换方向有点可惜,就打了个电话给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贺教授,问他:“你的研究生发榜了吗?我送份卷子给你看一下。”余教授看过试卷后说:“好,这个学生我收了。”就这样,我被录取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免疫学研究生。
谁知道过了一年,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,说这是学苏联的,不好,让我们都回去。于是临床医生都回临床去了,我想继续做研究,余教授就想把我介绍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去当助教。对我来说,不管北京还是上海,只要能做研究就好。但教育部没有批准,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,我就回到了上医。
1957年回上医后,因为我读了一年的研究生,不算56届,而是57届。按当时的规定,57届的大学生统统下乡。所以我的同班同学们在PG电子里当助教,我却去了浦东。
那时浦东还是一片荒芜滩涂。我们住在贫下中农家,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每天的任务就是挑泥、开河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。
“国家是需要知识分子的”
记者:到了60年代,情况是不是好转了一些?
闻玉梅:60年代初,周总理“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的提法广为流传,我们因此被叫回了上海第一医学院。风向变成了“好好学业务”,大家都要拜师,我就在这时正式拜林飞卿教授为师。
林老师不但手把手教我做实验,还教会我如何教书育人。记得我第一次试讲课,讲的是小儿麻痹症病毒,当时还不会上课,两堂课的内容半小时就讲完了。林老师对我说,讲课是要有很深厚的积累的,要广泛地阅读脊髓灰质炎病毒、小儿麻痹症病毒相关的书籍材料,把这些材料内化为自己的知识。
时光荏苒,到了1963年,林老师说,我能教的都教给你了,你应当换导师,继续前行。经过她的引荐,我踏入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,成为谢少文教授的学生。有人感慨,余贺、林飞卿、谢少文三位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泰斗都带过的学生,全国只有闻玉梅一个。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,我得到了诸多指引和成长。
但是,很快“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声音压倒了一切。谢老师被划为右派,扣上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”的帽子。那时候我经常在党内替他辩护,于是我就变成了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俘虏”,跟着老师一起挨批判。
批判了一阵子,领导放我回到上医。当时上医党委副书记问我为什么受批判,我解释说,因为我为老教授说话。他说,那不算什么,在支部自己检讨一下就行了,也没把我怎么样。
记者: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?
闻玉梅:上医领导确实很爱护知识分子。但我毕竟“犯了错误”,是“俘虏”,所以回来后不久,就再一次下乡了。
我先是在青浦的大队参与“四清”,后来又被调到工作团党委当秘书。我们秘书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写稿子。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青浦和金山采访农民、收集素材,跑遍了当地所有公社。有个老干部怕我不认路,就带我去采访,一路上给我讲沙家浜等革命故事。人与人的交流让下乡生活变得不那么乏味。
记者:什么时候重新拾起基础医学的呢?
闻玉梅: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回到了PG电子。一时间,校园里到处可见批斗的场景,林飞卿教授被当作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被赶去打扫厕所,我也一直以助教身份度过了这十年。
算起来,我一共当了17年助教,迟迟没升讲师。人家问我,你当时是怎么想的?我说,我想国家总归是需要知识分子的,不可能一直这样。所以我做助教的时候,也以副教授的标准要求自己,从不懈怠。
当时,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十分低下。为了响应中央号召,1967年,上医组织了“指点江山医疗队”,到贵州山区展开医疗卫生工作。为了支援这支小分队,1969年PG电子又派出了一支“教育改革队”,我也随队来到贵州。
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,人无三分银”,说的就是当时的贵州。那里山路崎岖、交通不便,我们挑着铺盖翻山越岭,刚开始还披件雨衣,后来雨衣也穿不了,只好穿着湿衣服赶路。
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后,食物非常匮乏,我们吃了三个月的盐水泡饭。老百姓起初不搭理我们,后来觉得这些医生不错,可以治病救人,还送他们肥皂等生活物资。后来有一次,他们送了我们一个南瓜,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。
还有一次,我和妇产科的学生去给人接生。在当地人的观念里,生孩子是脏的,要去猪圈生产,接生也不消毒,很容易造成母婴感染。我们把产妇带到了一间相对干净的屋子,没有脐带剪,就用碘酒擦拭后的旅行小剪刀;没有扎脐带的线,便把破被子里的棉线放到锅里煮过消毒,再用来扎脐带,最终产妇顺利生产。
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让我深刻认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。回到上海后,为了改善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,我接收了不少来自贵州等地区的进修生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回去当了赤脚医生。

闻玉梅(二排右一)在贵州培养赤脚医生
为国育人,一代会比一代强
记者:改革开放后,国内外交流日渐活跃。1980年,您受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全球病毒学术大会,还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学者提问。当时是怎样的情形?
闻玉梅:那是我第一次出国。当时我已经开始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,机会难得,但出国手续烦琐,尤其外汇很难搞。上医党委副书记冯光表示,除了给人磕头,我们会用尽一切办法申请到外汇。后来惊动了市领导,在市领导的关心下,市政府为我特批了一笔费用。冯光说:“这是人才投资。”这句话,我记了一辈子。
到了纽约会场,满座都是金发碧眼的权威专家。我没什么发言资格,但我想,国家投资我,我连声音都没有,怎么可以?所以当时虽然没想好问题,我还是举起手来抢话筒。
拿到话筒后,我开口说:“我是闻玉梅,来自上海,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全场哗然,因为当时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很少见,更别提主动发言的了。后来中场休息,许多华人科学家都跑来找我,介绍我去实验室参观,就这样打开了交流局面。
如今,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,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走出国门,在国际舞台上发声。我们不再妄自菲薄,却也不能过于骄傲,要坚持实事求是,以开放的胸怀努力融入世界、引领世界。

80年代访学期间照片
记者:您对现在的年轻学生有哪些期待?
闻玉梅:我们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。现在的孩子都太乖了,一堂课下来,老师问有没有问题,回答往往都是“没有”。我在做学生时,谢少文老师经常鼓励我提问。他说,不能光带着耳朵听,一定要提问,不提问就说明你听的时候没动脑筋。所以我养成了抢提问题的习惯。
年轻人要敢于提问,哪怕提的是笨问题也没关系。我这个岁数提问要掂量掂量,你们怕什么呢?另外,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提问,下课后可以多讨论,带动大家一起思考。我常跟学生说,我不一定好,你比我更好,一代会比一代强。
记者:前些年,您花了很多精力在“人文与医学”慕课上,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?
闻玉梅:这些年来,我们建立了实验室,培养了一批人。年轻一代的学者飞速生长,已经超越了老一代学者。我内心充满欣慰和自豪,可是也不能白坐在家里。
2014年前后,伤医事件频发,舆论对医生群体也不太友好,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工作,引导人们建立医学哲学思维和医学道德观念。所以我“80岁老人学吹打”,拉上彭裕文、俞吾金两位老师,为复旦学生开设了一门《人文医学导论》研讨课。
课程很受欢迎,吸引了各个专业的学生,旁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。为了让更多人受益,我们推动研讨课成为网络共享课。目前在500多所高校推广,超20万学生注册学习。

2003年4月22日,闻玉梅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、病毒学专家Wolgang Presie(左起Wolgang Presie、袁正宏、闻玉梅)
最重要的信念
记者:您最近在忙什么?
闻玉梅:我最近正在策划一本关于老年健康的科普书。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,我经常思考,怎样减少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负担?健康老龄化、快乐老龄化或许是一种思路。
循着这个思路,这本书的书名就叫《智慧老人的健康密码》。我们请了各领域的顶尖医疗专家,通过最专业的人讲透老龄化的本质。我告诉这些专家,每章只能写4000字,力求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科普学科最前沿发现,让老人和家属能够根据指导行动起来。我们争取今年年底完稿,明年出版。
人的一生很短暂。我马上就91岁了,脑子不见得会再这么清楚了,能做一点就做一点,做不了的时候尽量不要拖累社会,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。
记者:您曾说“我是一名步行者”,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走来的路,作为“步行者”的感受如何?
闻玉梅: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是一条漫长、艰辛但又充满希望的道路。新中国走过的苦难和艰难我都经历过,可我始终深信不疑:中国是有希望的,中国会强大的。我们要有信念,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国家、相信党,不管出了什么事,走了多少弯路,国家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,会带领我们前进。这个信念不可以没有。
眼下大家有很多困惑,特别是我们的青年,正面临种种人生难题。我想,国家在找办法,我们自己也要找办法,努力走出困境。无论如何,我经历了那么多起起伏伏,有时候很快乐,有时候觉得很艰难。但是再艰难,总归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,总归要为中国人民做事。





